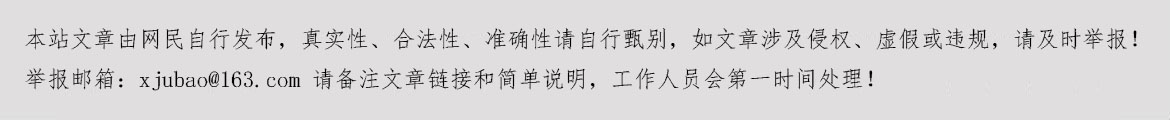▲ 5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相关领导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才扬/图)
数据显示,中国整体人口素质、受教育程度在提高,性别比偏差在逐步缓解,城镇化加速,总人口超过14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2020年新出生人口1200万,也预示着未来低生育率的困境。
低生育率对于东北人口萎缩造成的影响,远大于人口流出的影响。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敬奕步
2021年5月11日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人普”)主要数据结果。
据通报,中国人口共141178万人,比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简称“六人普”)增加了720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0.53%,相较“六人普”下降0.04%。这表明,中国人口十年来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人口性别结构相较“六人普”得到了改善。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七人普“从2020年11月1日到12月10日进行入户登记,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随机抽取141个县的3.2万户,主要调查人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婚姻生育等。漏登率为0.05%。
据央视新闻,“七人普”是历次普查中、项目数量最多最细的一次。比“六人普”增加了身份证号码登记、3-6岁学龄前儿童受教育情况、60岁以上人员居住情况等指标,同时采用了以电子化采集数据方式开展人口普查登记等新技术。
如何解读“七人普”相关数据?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人口学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人口经济学家、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以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卢晶亮。
1
“生育率确实非常低”
南方周末: 你认为本次公布的数据中,最重要的数据是哪一项?如何解读?
梁建章: 今天上午公布了很多信息量很大的数据,有些数据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中国的整体人口素质、受教育程度在提高,性别比偏差在逐步缓解,人口流动也是我觉得非常符合预期地往东部流动,总人口超过14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是有个数据还是非常令人担忧——2020年的新出生人口,也预示着未来低生育率的困境。
刚公布的数据是中国2020年共出生1200万人,近几年来新出生人口迅速下降,从2016年刚刚放开二孩的时候生了1700、1800万人,目前只有1200万人,下降了1/3,下降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比2019年下降了差不多18%。
在一代人以前,也就是1990年代末的时候,一年最高可以达到2900万,现在只有当时的一半,这说明我们的生育率确实很低。换句话说现在应该是生育高峰,因为30年前1990年的时候生了将近三千万人,现在只有1200万人,所以现在的生育率确实非常低。
生育率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呢?今年也公布了中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3。我们详细拆解下1.3这个数字,它包括了相当部分的堆积效应。二孩开放以后,有些人原来想生二孩,由于当时没开放,到二孩开放补生了一批。堆积效应是短暂的,几年以后就没了。
去除堆积效应以后,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应该只有1.0-1.1左右,这比日本生育率1.3-1.4低很多,应该可以说是全世界垫底的水平。日本是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而我们的未来生育率,估计更悲观,因为不光是堆积效应消失了,而且育龄妇女也减少了,随着城市化继续进行,我们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还会进一步下降。
这样的生育率跟其它国家相比怎么样?现在的水平已经低于日本,跟韩国水平差不多,韩国现在是垫底的1左右,欧洲差不多1.6,美国更高些。
现在我们生育率虽然已经是很低,但确实还不是底,如果未来没有强有力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肯定比日本低很多,而且确实有可能是世界最低的。
卢晶亮: 我比较关心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流动人口规模与分布。202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达63.89%,较2010年上升14.21%。流动人口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69.73%;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占比88%;而在跨省流动的人口中,流向东部地区的占比73.5%。
这表明,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化率提高较快,人口向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明显。以广东为例,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达到8.93%,十年间人口增长20.81%,经济发达程度决定了对人口的吸引力。
未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继续提高依然是大势所趋,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相对落后。给我们的启示是,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规划应该以常住人口规模为依据。
南方周末: 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该如何解读?
卢晶亮: 二孩出生占比高是以往受限制的生育意愿的逐步释放,但是“二孩”效应已经逐步减弱。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婚姻推迟导致的生育推迟、养育成本等因素都会抑制生育意愿。
2
东三省人口负增长
南方周末: 据七人普数据,在全国大部分省份人口都在增加的情况下,东北三省仍呈现负增长。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易富贤: 东北的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十多年。东北年轻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人们却误以为是人口外流。但其实东北人口流出、流入大致平衡。
其他省份例如广西的劳动力流失率远比黑龙江高,但由于生育率较高,补充了劳动力,留在本省的20-39岁人口占比仍然稳中有升,经济占比也没有像东北那样大幅下降。
东北的老龄化危机也率先爆发。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2019年东北的GDP与2012年一样多,意味着7年经济零增长。
东北经济衰退的原因很多,但核心原因是他们不再“造人”了,“人口制造业”的衰退必然导致“物质制造业”的衰退。
黄文政: 第一,东北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农村人口比例低。第二,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国营企业较多,当年计划生育执行得很彻底。第三,东北没有南方那样深厚的生育文化。
需要指出一个常见误区,很多人认为东北人口的萎缩是因为人口流出,实际是过去长期低生育率造成了年轻人口的消失。低生育率对于东北人口萎缩造成的影响,远大于人口流出的影响。
南方周末: 公布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8.8亿,但与2010年相比,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多万人。如何看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现象?你认为人口红利还存在吗?
卢晶亮: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抚养比较低这样一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从数据上看,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63.35%,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从未来发展的需要来看,我国应该尽快促进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也就是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老龄人口的比例在上升,但老龄人口的人口素质也在提升,要充分开发老年人口的劳动力资源。
南方周末: 按照惯例,统计局人口普查会先公布几项主要数据。之后出普查年鉴,才会有详细数据。这一次未公布的数据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
卢晶亮: 未来期待公布各省之间详细的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向、各省分城乡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生育率等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3
“少生快富是不现实的”
南方周末: 为什么生育政策放宽,效果却难以达到预期?
黄文政: 中国的生育率一直非常低,尤其城市里,已经把生一孩当成默认选择。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会进一步降低。
这里面有一个恶性循环:只生一个,家长把所有资源都放在他身上,为了不让小孩输在起跑线,这就导致大家教育竞赛,把养育模式彻底改变了,不可能去养更多小孩。
梁建章: 几十年前,中国比现在穷得多,但抚养孩子的成本比现在低得多,尤其是教育成本。
那时孩子很少上补习班,大部分人也不上大学。而且那时的农村人口比例较高,城镇化率比现在低得多。例如,1978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8%,而2019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0%。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城镇化率越高,生育率越低。
如果仅放开生育但不鼓励生育,生育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因为现在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太高了。要提高生育率,需要出台鼓励生育措施以切实减轻育龄家庭的育儿负担。
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就是压抑年轻夫妇生育意愿的两个重要因素。有两种解决措施:
一是对多孩家庭买房补贴,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比如对于二孩家庭可以部分免除地价。
二是缩短学制,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合并,缩短为中学四年;将大学教育分成基础的本科3年和研究生3年。
减轻年轻人养育孩子负担的具体措施则包括:
第一,政府对养育家庭提供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以直接发放育儿补贴。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现金部分,建议给多孩家庭支付大约每个孩子每年平均1万元左右的育儿补贴。另外对于二孩和多孩家庭,还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
第二,大力建设幼托设施。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建议把0-3岁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做到这点,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约十万个幼托设施。
目前生育率普遍高于中国的欧洲国家,将GDP的1%-5%用于家庭补助。数据表明,家庭补助占GDP的比例高1%,生育率大约高0.1左右。
南方周末: 人口增长慢、生育率放缓是否存在积极影响,比如提高人均资源?
梁建章: 长期低生育率对国家和社会是有害无利的。一个国家的贫富不是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高低。例如,很多非洲国家人均自然资源丰富,却是穷国;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虽然人均自然资源贫乏,却是发达国家。
人均GDP的高低取决于生产效率,一个社会的技术和组织效率基本决定了其人均GDP水平。在同样的技术和组织水平下,人口越多,GDP总量就越高。比如,在欧盟内部,除了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欧和东欧外,其他国家的人均GDP都差不多。这也说明了减少人口并不能提高人均GDP。
另外,减少人口也不意味着就业竞争的压力会减少,因为就业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少了,竞争者少了,机会也变得更少。人们从乡村去城市,从西部去东部和南部沿海,都是从人少的地方去人多的地方找工作。如果人少了真的有利于就业,人们只会反向迁徙。
黄文政: 东北原来人均GDP比全国高39%,非常富裕,现在比全国低34%了。
所以少生快富是不现实的,少生不可能变富有。经济本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少生,经济活动的效率会降低,技术进步的速度会延缓,劳动力也会相对萎缩,怎么可能会变得更富有?
而且资源是人开发出来的,价值是人创造出来的,“少生”所有的好处都是短视的,长期来看只有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