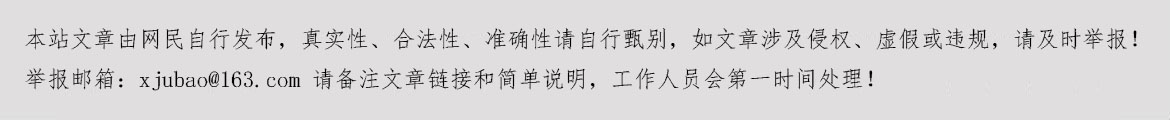作者:潘绥铭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性的背后是生命》,说的是:性,贯穿于人的终生,标志着生命的价值。现在有了全国18-61岁总人口的四次调查的统计数字,我就可以更详细地说一说“性的生命历程”啦。
但是首先必须说明:一切统计出来的平均数,都仅仅是为了知道全体中国人的整体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绝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是这样的;更不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向这些数字“看齐”,千万不要因为看到下面这些数字就骄傲或者自卑。
1.性的春天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性发育(青春期)来得越来越早。从2000年到2015年的短短15年间,在18-29岁的总人口里,男人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提前0.6岁;女人的月经初潮则因为已经非常早了。所以只提前了0.2岁。
如果从代际差异来看,那么在2015年,那些50-61岁的男人是在平均18.1岁才开始首次遗精,比18-29岁的男人晚了2.4岁;50-61岁女人的月经初潮则是晚了1.4岁。
这就给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那些青春期迟迟的老年人,来管束那些性发育提前了2岁左右的青年人的性活动,是不是有些荒谬呢?尤其是,还会有用吗?
2.性的秋天
人越老,性生活就越少,这是人们的常识。但是具体的情况如何呢?请看下图,说的是2015年的情况。
上图表明:在55-61岁的男女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性生活频率已经下降到每个月最多一次了。可是也请不要忽视:即使到了55-61岁,也仍然有8%的男女可以保持每个星期性交3次或者更多。
如果反过来看,那么平均起来,人们到了多大的年龄,还可以保持什么样的性生活频率呢?请看下图,也是2015年的情况。
上图说的是:可以每天至少性交一次的那些人,平均起来是36岁,每个星期过1-2次性生活的人,平均是40岁,每个月最多有一次性生活的人,则是平均48岁。
这就提醒我们,人们平均起来的性生活频率,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低。尤其是,中国人在一生中的“性寿命”(性活跃时期),也比大家预计的要短得多。平均起来,刚到48岁,中国人的性生活就已经“退居二线”啦。
3.性的社会历史发展
以上说的仅仅是2015年的情况,可能有些令人悲观。但是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那么情况就会乐观得多。请看下图。
从2000年到2015年的短短15年间,在18-61岁的总人口里,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人(每个星期至少3次)增加1.4倍,达到五分之一,应该说是非常多了。相应地,低频率的人(每个月最多一次)则减少60%,降低到仅仅五分之一,已经算是很少了。因此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整体性生活频率是明显地增加啦。
这显然不仅仅是由于生理因素的变化,因为对于14亿人这么大规模的总人口来说,任何生理因素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齐刷刷地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性生活的增加,主要应该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就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性化”进展。
它说的是: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和现象,与“性”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整个社会日益走向“性无所不在”的局面。结果,“性生活很宝贵”这样的新观念也就日益普及,不仅在年轻人中间已经成为共识,而且中老年人也在奋起直追。
正是在这种新文化的耳濡目染和细雨润物般的渗透之下,人们才可能在生理因素没有大变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性生活之中。
性的最后信仰
在历史上,我们中国人的性,时时处处受到各式各样的控制,大到法律、道德、习俗、传统;小到家庭、朋友、环境、时机等等。别说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切,就连足以改变其中一两项的人,恐怕也是寥若晨星。于是,我们所崇拜和追求的“性福”,其实只不过是“笼中凤凰”,区别仅仅在于笼子的大小。
但是最近30年来,中国的性革命风起云涌,至少已经在一部分人口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决和消解了以往的那些控制,性的自主与自由似乎已经喷薄欲出。
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这样做呢?其实在目前,抑制着“性自由”的思想力量,既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精神文明,更不是爱国主义,而是爱情,是那种自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深深植入中国人心中的浪漫情爱。
自从1991年开始,我就6次调查中国大学生的性关系与性行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提问就是:在性方面,无论你现在做到了哪一步,你为什么没有继续做下去?究竟是什么阻止了你?答案当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双方的感情还没到那一步;也就是说,爱情还不足够。尤其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1世纪,虽然有所减少,但是仍然占据主流。
与此相类似,在21世纪对于全国成年男女的三次调查中,已婚者中间所谓的“婚外性行为”,其实主要是“婚外恋”,是出于爱情才“出轨”。这其实不难理解:很多丈夫或者妻子,敢于不计后果,敢于承担后果,非要去做,恐怕只有爱情才能激发出这样的决心吧?
反过来看,所谓的“剩女”,其实并不是“条件太高”,她们最主要的动机是坚守自己的爱情标准,绝不迁就。就连在我们最近举办的“老年知性恳谈会”上,主流意见也同样是:可以无性,不能无爱。
总之,目前的多数中国人,仍然是:因为爱,才上床;因为爱,不上床;因为爱,无需床;因为爱,重搭床。
这就是“爱情至上主义”。把它归结为“性自由”,实在是太冤枉了。即使在那些看起来最自由的性活动中,例如“一夜情”,虽然爱情可能不够多,但是却足以对性行为多了一层筛选。
以上分析的是现状,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从价值选择上来说,该如何评价呢?
我们不要忘记了: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就是“对于爱情的幻灭”。
爱情当然好,但是它不仅可能是“可遇而不可求”,还可能是“月有阴晴圆缺”,更可能是“几人可得之”。例如在我们的调查中,已婚者觉得爱情很充分的人,只不过刚刚达到一半。那么另外一半的人该怎么办呢?虽然“心灵鸡汤”漫山遍野,但是终归会有一些人因为爱情太难,只得退而求其次,去寻求“性的快乐至上主义”。从目前情况来看,这样的人只会不断增加,没有任何减少的希望。
总之,把爱情作为性的最后信仰,虽然是现时中国人的选择,但是正因为它是最后的,因此必然会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可惜,这样的预测,就连听我的课的大学生们也难以忍受。他们呼吁我:请不要剥夺我们最后的这一点点信仰!
可是,这究竟是一种宣誓,还是一种悲鸣?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文转自潘绥铭的博客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从1985年开始,在中国创立与推广性社会学,主要是在连续的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下,奠定了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基本概念:初级生活圈、中国性革命、性产业、亲密消费、性生活的内在矛盾等。他提出“全性”(sexuality)的研究范畴,主张在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中,在情境、互动与变化中,研究其现象及意义。他还主张:“全性”与“社会性别”(gender)是相互建构的、不可分割的。